《带我去远方》是金钟奖最佳编剧傅天余的长片处女作,影片以一贯的台湾小清新感觉,在日常生活的碎碎念中,讲述了色盲小妹“阿桂”和同性恋“贤哥哥”的童年往事和残酷青春,呈现了社会中被化为“边缘”和“异类”的人群对一个没有歧视没有屏障的乌托邦之梦的追求与失落。
影片的开场,阿桂跟着阿嬷去买菜顺便去姑姑家看贤哥哥,色调淡淡的却在水宝宝的瓶子中反射出童真的五彩斑斓,水的流动,孩子的童真,概括了童年回忆的美好,也为阿桂的色盲埋下伏笔。因为色盲,她总是买回绿番茄而被阿嬷责骂丢了魂,也是因为色盲,总有调皮的小伙伴讥笑她,后来学习美发,也因为对色彩超现实的把握遭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孤立。在这样的孤独中,贤哥哥是唯一能理解阿桂的人,因为贤哥哥也是被社会孤立出去的同性恋者,他铺着地图地毯,他喜欢读世界各国的趣闻轶事,他爱上远方来的旅人,爱上巡海员,他努力学习英文攒钱,渴望去纽约和巡海员开始自由的生活,却无奈在内心的挣扎中,在宗教的谴责中,自杀未遂成为植物人。
一对兄妹俩一个是半色盲,一个是宅男同性恋者,又住在远离大都市的小城镇,影片的人物和场景立场都是边缘,在电影中却逆转为中心,主流社会却彷佛成了剧中的边缘。这样的视角通常意谓着两种语调:一种是出离世外的浪漫向往;另一种则是不论有意无意,往往都会达成的一种审判。越是边缘的立场,越是离社会结构的中心,当他们被逆转为话语的中心时,往往是一种叛逆于社会主流的观念树立,或是为法官筑起了高桌子,赋予了一种审判的权力,让他得以站在系统的边缘,以纯洁的心灵,对整个系统内的社会人进行审判。剧中的两位主人翁虽然只是渺小人物,却有纯洁天然的心。这是边缘审判者意象的现代化,完成审判,却不用强力。
阿桂不仅仅是简单的半色盲,她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与我们常人眼中相反的颜色。色彩语言的隐喻在作者的设计下被巧妙的一语双关了。对于阿桂来说,真正的世界不是红绿分明的,红绿混郩的世界才是她真正的天然世界。绘画的本质就是要画出自己眼中,心中独特的视角和景像,黄色的天空,红色的树叶有甚么不可以?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而言求之不得。可是她出生的这个社会环境,除了阿贤哥哥和父亲之外,从没有人体谅过她,更不用说尊重她。老师和家人都认为是一种病,想纠正她;阿嬷也是认为她脑子不好,要不然就认为她丢了三魂七魄。而阿贤哥哥和父亲(送给阿桂一堆各色太阳镜,这样就能看见各种颜色了)能够体谅她,也是因为他们本来也是社会中的边缘人。
阿贤原本看似想要从这样边缘的角落进入到社会的系统中去,而且还是社会系统中最中心的地方,在纽约;晓桂想去的地方却比她所处的边缘更边缘,在平格拉普岛。但他们的梦想却都是让自己不再边缘。本质上依旧是想要进入一个社会的系统中去——以自己本真的状态受到社会认可。然而结局阿贤的梦碎,他畏惧现实,格格不入,止是想沉睡,于是便真的沉睡,他在这个世界边缘得接近彼岸,又在彼岸的世界中边缘得接近此岸,囿于两个世界的夹缝中。阿桂的梦也无法完成,于是她向这个社会妥协。“一个人只要很快乐,就可以忍受任何的规律。”并不是去忍受任何的规律,就可以让自己变快乐。她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彷佛有一点懵懂,又或许是她的颜色总与他者颠倒,于是她也想试着颠倒这句话。她只需要自我分裂,颠倒自己眼中的颜色,便可以在美发考试拿很高的分数。这不是我们很熟习的么?撒谎换来的分数,违背自己内心换来的认可,但是就像阿桂自己说的“我感觉我变老了”。
影片中我们看到两个边缘的主人公都在努力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失败了,不是在梦想的失落中逃避自杀就是靠牺牲自己对世界的判断换取短暂的认同,但电影中就像从未正式露面的凶手,这就足以窥见社会的侧影。朴素的生活和人群就足以压垮他们。影片通过两位主人翁的无助,以及他们的人格牺牲,张开了旁观者的道德领域。如果我们陈腐的观念得以改变,我们是可以帮助他们的。一个观念的改变就使得社会变得更好,这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带我去远方》是向你的一个责任邀约。是的,是由你来带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太平洋的的色盲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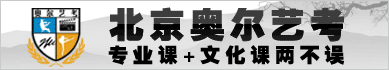









 1124768988(合作加盟)
1124768988(合作加盟)